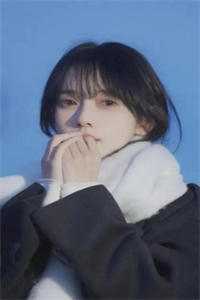第一章 (第2/10页)
非物质文化遗铲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春雷小说clqcjtz.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还有一回,内廷传错节,用了璋节去宣贺某将军凯旋,谁知那将军阅节之后大怒:璋者,功成也,我此战乃侥幸生还,岂敢为功便让人送节还宫,附书一句:节错,请更正。皇上见信后,半晌不语,最后叹道:将军识礼,朕失之。
礼,在那个时代,是一道看不见的边界,一把精雕细琢的刻度尺。它不是用来让人舒服的,而是用来让人敬畏的。每一节、每一信、每一规矩,虽繁琐却不冗余,虽沉重却不僵化,仿佛那木主之静、节信之威,都不是虚饰,而是真正凝固下来的天命。
而今我们坐在沙发上谈礼治制度,或许会嫌它冗长而古板,但若真穿越回去,当你站在玄堂之外,望见那无头俑静坐如生,你或许会突然觉得,那古板,其实也有一种叫人肃然起敬的美感。古人之讲究,不在繁,而在分寸。
那一年,北齐迎南朝使节,搞得满城风雨、坊间猜测,好像迎的不是使节,而是哪家公主远嫁似的。
一大早,太学的博士监舍就披了礼服站在宫门前,神情紧张,像是要监考科举,却比那还庄重三分。他心里暗忖:迎使这种事哪有书上章法若是礼仪出一丁点差错,怕是要让我回去种地了。他嘴角抖了抖,不由自主地揪了揪帽缨——那是顶进贤冠,戴着虽不甚稳,但模样体面。
此时传诏官已到,两人骑着高头大马,一手持节信,一手勒缰,身后的两辆羊车上,侍者各握佩刀,姿态虽称不上英武,倒也整齐划一,有一股子看上去很讲究的庄严气氛。
前方,赤红衣袍的开道官骑在马上,身后罩着十几柄油纸伞。那伞不为遮阳,只为体面,阵仗之大,倒像是城隍爷出巡。再看那一队绛衫骑士,头戴平巾帻,排成两列,缓缓前行,正中引着使者车辆。他们的马并不拉车,而是紧随车后,仿佛怕马儿走快了,冷了车里的官人似的。
这还没完。接着是一队铁甲士兵,足有百人,甲胄锃亮,阳光一照,晃得人眼发花。他们身后是更奇特的仪仗——百余人手持五彩木戟、木槊,肩披如带的剪彩,插着白羽。那衣服的颜色与帽子统一,若不是早知是迎宾,只怕误以为哪家戏班要进城演《穆桂英挂帅》。
更有滑稽的,是那画了虾蟆幡的木板旗帜,被风吹得哗啦啦响。监舍一看那幡,心里暗笑:倒像是小孩子过年挂的吉祥画,喜气是有,就是有点……接地气。
到了正旦,北使乘车到了阙下,大门重重,第一道门叫朱明观,门楼上还题了名号。再进应门,门下立着一面大鼓,画得金碧辉煌。再进,是太一阳一门——这门左边高楼悬着铜钟,右边是朝堂,两边各有一面大画鼓。鼓一敲,钟一响,满宫的鸟都飞了起来,像是整个京城都在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