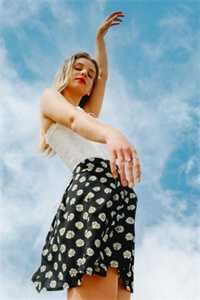第四节 西域 (第4/8页)
施展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春雷小说clqcjtz.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中亚的地理破碎性,不仅使得外部难以持续地统治它,在其内部也始终保留着自由,这在欧亚大陆东、西部的传统帝国当中久已被消弭掉。中亚所保留的自由,在较小的意义上,呈现于中亚游牧帝国的军事贵族制始终未被赎买;在较大的意义上,呈现于中亚定居地区的诸多城市,彼此互不统属,也不长久地被外部世界直接统治。集权秩序在这里难以持续,一个个互不统属的自治共同体,构成了超越单个绿洲城市之上的自生秩序。这不是政治哲学意义上建构出来的自由,而是一种社会风俗意义上的源初自由。
中亚地区的自由特征,天然地适合于贸易对自由秩序的要求,可以说,“自由通道”就是中亚地区的世界历史命运,其破碎性成就了它的这种命运。中亚因此有了一系列以经商而闻名的定居城市,如河中地区的花剌子模、撒马尔罕、布哈拉、玉龙杰赤,以及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和田、叶尔羌、库车、鄯善等等。
中亚的商人群体要依赖游牧帝国或轴心文明帝国的保护,但这些商人在古代一直到中世纪都大有能量。比如,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中亚商人群体粟特人,他们先是依赖于大唐,后又依赖于回鹘帝国的保护,但正是他们的商业活动,才使得自己的保护者的军事后勤运输工作乃至战争融资活动成为可能。在回鹘帝国时期,粟特人成为其最重要的参谋,他们帮助回鹘人制定外交方案,规划军事战略,因自己的商业需求,而试图引诱回鹘去与拜占庭帝国建立联盟关系以打压萨珊波斯帝国,或是帮助回鹘帝国策划如何压榨安史之乱后国道中落的大唐,等等。<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王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7—168页。">
在中亚逐渐伊斯兰化之后,信奉摩尼教、祆教等波斯系宗教的粟特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是中亚的萨尔特人。萨尔特人很可能就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粟特人后裔,当然,他们已经混入了突厥人的血统。据俄国突厥史权威巴托尔德的研究,在11世纪,萨尔特人形成庞大的商人团体,其发行的支票甚至比政府支票的信用度还要高,check(支票)这个词最初是在这里出现并作为外来语传入欧洲的。<span
class="mark"
title="[苏]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第134页。">
中亚庞大的商人群体,不受这个地区走马灯般的政治变换之影响,一直在进行跨境的商业活动。丝绸之路上,运输的商品可能很多产自中原,但真正从贸易上控制这条道路的,是中亚商人。这种基于贸易的世界史,更形呈现出政治与战争之外的一种深层结构,让我们意识到,轴心文明地区以及游牧帝国与中亚地区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
从文明传播的角度来讲,中亚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