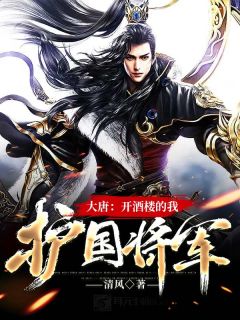第三节 从普遍帝国到普遍人民 (第13/20页)
施展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春雷小说clqcjtz.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span
class="bold">1.对普遍均质人民的历史需求
区别于西域或者北族,西方世界对于中华帝国的普遍精神理想与秩序所带来的冲击,从精神与物质这两个层面都是全方位的、根本性的,以至于这个普遍帝国在本质上被还原为特殊性的存在,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忧虑于国运者,发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呼唤。这一点上,稳健派的张之洞与激进派的康有为并无分别,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曾明确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三事一贯的主张,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更是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其基本宗旨。
这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与精神情境。在过去,“教”是普遍主义的理想,超越于具体的时间与空间,不以任何特定的国家与人口为依托,孔子不惮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因为“教”所要传承的“道”,本就是属于全天下的。“国”则是个特殊的存在,它只能存在于具体的时间与空间,显然是无法与“教”相提并论的。至于“种”,所指代的是有着内在同质性的一个人群,在传统时代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种”的观念,更多的是“君子”“小人”之分,这里不存在同质性的人群,而是一种差序格局,孟子甚至抨击欲图抹平差序奉行兼爱的墨子学说为无视君父的禽兽。<span
class="mark"
title="“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参见《孟子·滕文公下》)">故而,顾炎武曾区分了“国”与“天下”,并在差序格局下提出了不同位置的人所应担负的不同责任:“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但是,西方的冲击使得中华文明全方位地沦入特殊化的境地,国人猛然发现,“教”与“国”实际上是一体的,儒家所想象的天下,差不多也就仅限于中华帝国的范围所及,国家兴亡与天下兴亡从而变为一回事。于是,古人所谓“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转化为今天中国人所熟悉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与天下的等同,就会带来君子/肉食者与小人/匹夫的等同。紧跟着的结果是,君子与小人的差序格局在这种观念的转化当中,被削平为同种同源的均质化共同体,“种”的观念于是浮现出来;如此一来,国家的主人,便也不再是“奉天承运”而与平民之间有着质的差别的一家一姓,而是作为整体的“种”(人民)。“保国、保种、保教”在这一过程中融合为“三位一体”的观念。
因此,对于普遍均质人民的打造,就此成为中华民族之精神现象学运动的一种自然需求,成为这个曾经自视为普遍的、如今沦为特殊的帝国所面临的全新的历史使命。即便是稳健派的张之洞,也明白地提出:“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span
class="mark"
title="张之洞:《劝学篇》,第11页。">君子、小人的“风”“草”之德性差别,在这种“同心”当中,自然会被消解掉,转化为一个全新的信念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