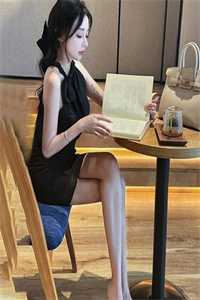红泪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春雷小说clqcjtz.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重新翻开书,手指竟有些颤抖。目光像探针,在字里行间急切地搜寻着。终于,在一篇题为《旧码头》的散文里,看到了那个曾经只属于我们两人的隐秘记号——一段关于江边废弃码头的描写。
石阶上青苔暗生,江水浑浊,打着旋儿奔向远方。一个旧木桩孤零零地立在浅水里,水波日复一日地冲刷着它早已腐朽的根部。不知是哪一年的洪水,在它身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记录着某次汹涌的淹没和退却。
我的呼吸骤然停滞。木桩上的伤痕!那是在我们一起散步的江边,一个黄昏,她指着那个半浸在水里的旧木桩对我说:你看那道疤,多像我们吵得最凶那次,你在我心上划的口子。当时我哑然失笑,笑她比喻得太过夸张,却又忍不住伸出手,轻轻拂过那道木桩上的深刻凹痕,仿佛真的能抚平什么。江水在脚下呜咽,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那一刻,她眼中闪过的水光,是委屈是释然还是某种我未曾完全理解的烙印这道伤痕,这个只有我们两人知晓的隐喻,此刻竟如此清晰、如此具体地呈现在这陌生的书页上。
再无怀疑了。这断句的习惯,这栀子花的低语,这木桩上独一无二的伤痕……所有隐秘的印记都指向同一个答案。书页上的字迹在我眼中开始晃动、晕染。我紧紧捏着书脊,指关节因用力而泛白。这薄薄的一册书,此刻却沉重得如同整个世界压在了手上。原来她一直写着,用另一种方式活着,固执地将那些我们共同经历的碎片,那些欢笑与泪水,那些刻骨的甜蜜与尖锐的疼痛,都熔铸成了文字——以杨时雨之名,以笔为刀,将过往的骸骨细细剖开,展露于世人面前。而我,竟在这毫无防备的雨日午后,一头撞见了这精心打磨的、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墓志铭。
我下意识地抬头环顾四周。书店里很安静,只有书页翻动的沙沙声和咖啡机低沉的嗡鸣。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围坐在角落的桌子旁低声讨论着什么,一位老先生戴着老花镜,专注地捧着一本厚书。收银台后,年轻的店员正低头整理着单据。没有熟悉的身影。心口那阵狂乱的悸动稍稍平复,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更深的茫然和一种巨大的、近乎失重的虚空。她在这里吗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如常生活,写着这些平静而又惊心动魄的文字还是早已远去,只留下这些文字作为航标,标记着她曾经过的航线我像一个在陌生海域突然发现了旧船骸的水手,既惊且惧,不知所措。
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那本书的封面,那个名字:杨时雨。这三个字,此刻像拥有了灼人的温度,烫着我的眼睛。我拿出手机,指尖悬在屏幕上方,微微颤抖。搜索框像一个无声的深渊,只需输入这个名字,只需轻轻一点,那些刻意回避的、尘封的过往,那些关于她后来生活的蛛丝马迹,或许就会像洪水决堤般汹涌而至。她的样子变了吗她现在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无数个问题瞬间涌上喉咙。指尖几乎要触碰到冰凉的屏幕,只需一个微小的动作,那扇隔绝过去与现在的门就会被推开一道缝隙。
然而,就在指尖即将落下的刹那,一股强大的力量猛地攫住了我,仿佛有冰冷的手扼住了手腕。勇气如同被戳破的气球,瞬间泄尽。我猛地缩回手,仿佛屏幕是烧红的烙铁。我害怕。害怕那搜索的结果会彻底打碎心底某个模糊而脆弱的角落。害怕看到陌生的、与我再无交集的生活轨迹。更害怕……害怕她早已云淡风轻,而我,却还固执地守着那堆早已冷却的灰烬。这迟来的探寻,除了徒增困扰,又能改变什么又能挽回什么过去像一只摔碎的瓷碗,纵然将每一片都拾起,那纵横交错的裂痕,也永远无法弥合如初了。再大的努力,也不过是拼凑出更触目惊心的伤痕。
手机屏幕暗了下去,映出我自己模糊而略显苍白的脸。窗外,雨势似乎更大了些,密集的雨点敲打着玻璃,发出单调而固执的声响。我缓缓地将手机塞回口袋,动作有些僵硬。那扇门,终究还是没有勇气推开。
我再次拿起那本散文集,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光滑的封面。这一次,我翻到了扉页,目光落在作者简介那一小块小小的区域。杨时雨,现居南方某城……南方某城。一个模糊的指向,一个安全的距离。心口那阵尖锐的刺痛感奇迹般地淡去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带着钝感的酸涩。她离开了,有了新的城市,新的生活,新的名字。这距离感,竟成了一道意外的缓冲带,让我得以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