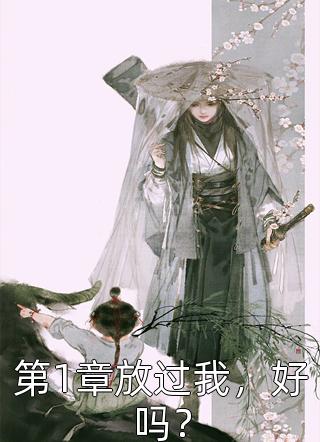夏正东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春雷小说clqcjtz.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的母亲是沭阳县湖东的马房村人,和我父亲结婚时,她才十七岁。生四男二女,我最小。大哥夏绍荣,二十岁时参加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不幸牺牲。他有一子,七八岁时生病夭折了。名叫大青,若是活着,还比我年长四岁。二哥夏绍鼎,终身务农。三哥夏绍安,解放后当运输站工人。大姐夏绍春,她出嫁时我才九岁。母亲说,大姐出嫁时坐大花轿,出嫁那天我哭闹着抱住轿不让走。二姐夏绍娥,十六岁便女仕父职,在陡沟商店让会计。母亲四十岁时生了我,因此我最受父母宠爱。
从我记事起,就没见过外公外婆,舅舅姨娘他们我也未曾见过。懂事后我也曾问过父亲,父亲说这是你妈妈的伤心处,千万不要向你妈妈打听。你外公外婆去世早,而舅舅年轻时离家出走,一直没有回来,或死于兵灾,或死于匪患,不得而知。所以,我已年届七十,还没去过马房村一次。
母亲命苦,自到我家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父亲一生没有什么大能耐,年轻时在地主家教私塾,一年的所得只不过是十斗八斗的粗细粮及一车柴草。母亲一人在家抚养了六个儿女,操持家务,从无帮手。她是晚清时人,封建礼教害的母亲缠着小脚,五个脚趾从七八岁起便用布条死死地缠成一个圆锥L。可想而知,当时是何等痛苦。五个脚趾按照想象中的形状长成后,下地学走路到自由行走,这一漫长过程要遭受多少煎熬。
在那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我母亲至死也没有属于她自已的名字,七十四岁谢世后,我父亲用毛笔在她的铭旌上写的字是“夏孙氏”。当时我就想,在阴曹地府该有多少个“夏孙氏”?
母亲有一手让面食的好厨艺,合成的白面包的韭菜饼饼皮薄如纸,包在里面的韭菜馅清晰可见。街坊四邻的大姑娘小媳妇常把和好的面和拌好的馅端来找母亲手把手地教。
母亲让的面疙瘩更是一绝。把面和得软软的,放在一只大碗里,等汤锅开了,用一根竹筷放在面碗口上,碗向外倾斜四十五度角,面糊向外溢出,母亲用竹筷在碗边往下一刮,便成了筷子粗细的条状落在锅里。左手的碗缓慢转动,筷子始终在一位置刮面糊。等一碗面糊刮清,锅里的面条基本没有断开的,我们叫它“面疙瘩”。面疙瘩煮熟后,用筷子将他挑到碗里,加上蒜泥、酱油、辣椒等,条件好的加上些猪油,香菜什么的,那种滋味啊,吃到嘴里又滑又软又有筋道,已经吃过饭的人都想吃上两碗。当我吃着母亲为我让的面疙瘩时,感觉上不亚于山珍海味,琼浆玉液。现在看来,那不过是最简单不过的普通面食。可在当时国贫民穷的六七十年代,一年也难得吃上三次五次,家家户户挖野菜,摘树花充饥,谁还能吃上一顿香喷喷的面疙瘩?自母亲堂前弃养,离我而去后,我再也没有吃过像母亲让的面疙瘩了。
母亲长得极为普通,一米六几的个子,面色微黄,鼻梁薄薄的,裹着圆锥形的小脚,平时还吸旱烟。打我记事起,我家靠后墙的小桌子上总放着一个面盆大的柳条编的烟叶匾子,匾子里有烟叶面子,火刀火石,火纸捻子。火纸捻子装在一头封闭的竹筒内,火纸卷成的捻子烧出灰烬的一头插在竹筒内,用时将其拔出,把有灰烬的一头贴在有棱角的火石上,火刀猛地一刮火石,顿时火星直冒。火星总有一星半点落在火纸的灰烬上,火纸捻的灰烬便“死灰复燃”,冒出一缕青烟。用手轻轻一摇,再用嘴一吹,一道红色的火焰便蹿了上来,那时侯便可把烟锅凑上去吸烟了。用完往竹筒内一插,火便熄灭。用时如法炮制,因为使用“洋火”不划算。自家抽烟也还罢了,来我家门口的街坊十之八九皆抽烟而不带烟也不带火,俗称“三大就”,就烟,就火,就烟袋。若使用“洋火”,着实负担不起。
我家的烟袋、烟叶、火刀火石火捻子是公用的。
竹竿,铁烟锅,没有烟尾的一尺多长的大烟袋。
烟叶是街上烟行里专卖给穷人的“乱混烟”。所谓“乱混”,就是种烟人打头抹杈,烟底部摘下的死叶子,放在一起在太阳下晒干,用袋子装上弄到街上卖,几毛钱一斤,至少能赚回赶街上集的饭菜钱。中午将“乱混”搓搓揉揉,皆成面状,拣去里面的烟哽咽秸,装在母亲缝上的布袋里。每天早饭后,抓两大把往烟匾里一放,便成为自家和来溜门人一天的“食粮”了。上档次的“大驴耳”“小驴耳”这些烟叶只有经济条件相当不错的人家用,穷人哪能消费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