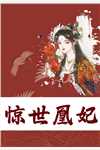第六节 西南 (第3/6页)
施展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春雷小说clqcjtz.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西南地区大山林立,其地质运动过程当中形成了丰富的矿藏。对于帝国政府来说,尤其有兴趣的是当地蕴藏的可用于铸币的各种金属。从元代中期开始,云南的银产量便冠于全国,直到清后期;明代,云南的铜矿又发展起来;清代,云南铜矿和贵州铅矿形成大规模开发,向内地大规模运输。由此,帝国政府便有了对西南地区进行直接统治的需求,在雍正朝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大量汉人为了开矿而向滇、黔地区移民,为帝国在当地设置流官时所需的税收财政奠定了初步基础。
但是,帝国政府的政策改革无法取消地理约束所带来的政治效应。西南的总体经济机会有限,所以汉人向西南移民的总数也是很有限的。流官由移民身上所获得的财政规模始终不大,从土著身上能够收到的税赋则成本高昂,甚至向其收税经常会充满危险,因此流官无法拥有向下贯彻其统治意图的基层官员。以黔西北的彝族地区为例,社会基层的原住民仍然认为地方的土著首领才是自己的统治者,帝国的流官反而缺乏权威,各种征徭与命盗案件,只有委托土目,才能顺利处理。<span
class="mark"
title="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88页。">
帝国对于西南地区的直接统治,仍然只局限在若干个点和线上,无法覆盖到面。
但是,帝国力量的进入,对于当地原有的政治社会生态构成了外生变量,两者开始了相互塑造的过程。仍以黔西北的彝族地区为例,在历史上,当地土著首领的权力继承关系并不是父终子及的规则,对应地,当地的家族结构以及世系的记忆,都与这种多样化的继承结构相关联。这与草原上不能父终子及的继承原则有所类似,但并不相同。草原上主要是为了确保首领的战斗能力;山区里更主要的是为了形成更加灵活的家族结构和财产分配结构,以便于迁徙,规避其他统治力量的干涉。随着明帝国统治力量的进入,当地的继承规则从明中期开始转为嫡长子继承的父终子及制度。<span
class="mark"
title="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第110页。">
这意味着土著部落内部的权威结构发生了变化,家族结构和财产分配结构也发生变迁,从而意味着整体社会结构必将经历改造。过去那样一种灵活的、易于规避外来统治的社会结构无法再持续,帝国力量得以继续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