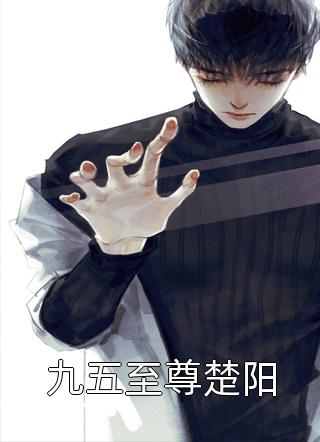第三节 大陆普遍帝国及其绝唱 (第28/31页)
施展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春雷小说clqcjtz.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span
class="bold">4.朴学与实学的精神逻辑
大清继承大明的理想,将理学规定为帝国的官方学说。相应地,理学建制化所致的制度性专权在大清也达到极致。这带来了治理的绩效,康雍乾盛世延续百余年;也带来思想的控制,盛世中伴随着各种文字狱,乃至人们在文字言谈中要做各种自我审查。<span
class="mark"
title="王汎森先生对此做过大量的细致研究。参见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于是,大清的思想运动转向工于考据的朴学。
朴学通过对于古典文献的考据,通过对于字词句义的分析与把握,谴责宋儒的“理”并无古典根基,并重新肯定“礼”的重要性。但朴学大师们所思考的并不是汉儒所关注的内含谶纬的“礼”,而是用以构建人际关系之行为规则的“礼”。大清的思想控制,反倒使得一种关注程序正义的精神要素浮现了出来;同时,个体的价值也因此在程序当中获得关注,以至清代朴学大师戴震在晚年批判宋明理学“以理杀人”。
由朴学的兴起,反观宋代以来的思想史变化,可发掘出其内在精神逻辑的一条线索。印刷术在北宋大规模使用以来,文化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君主可与民间结盟,但同时也会改变民间的社会组织机制,乡绅阶层在此过程中崛起。通过宋代理学的发展,可以看到政府与民间在效果与意图上相向的两种努力。一方面,君主制下帝国的观念统一得以推进,包括从北宋开始的禁绝淫祀的各种努力——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另一方面,民间也形成了新的用以约制君主的组织机制,乡绅遵守的严格的族规乡约,便是其组织力量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因为理学之下乡村宗族组织的顽固性与不通融性,才带来其组织能力,从而让社会获得力量,可以对集权秩序的制度性专权形成某种制衡。倘若宗族组织可以任意通融,则面对集权秩序的压力时,地方无法自我组织,从而无力抗拒。戴震所痛斥的“以理杀人”,很可能是不得不为此付出的代价。<span
class="mark"
title="这与清教自治共同体的内部严格纪律相类似。人们经常说是清教带来了现代的自由,但若仔细辨析的话,会发现,清教所带来的自由是政治层面的自由,其另一面便是社会层面自治共同体对于个体的专制。正因为社会层面的专制,才带来了社会足够强的自我组织能力,能够抗拒政治层面对于社会的专制企图。一旦在社会层面上的这种专制没有了,个体确实会在一般行为上感觉更自由,却不得不面临政治专制这种更可怕的风险。社会专制与政治专制的区别之一在于,面对前者,个体可以低成本地用脚投票,来决定是否接受它;面对后者,个体用脚投票的成本则高得多。">